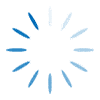时之序很久没生过病,这一回却在后半夜烧得厉害。
江燧先是被她断断续续的呓语吵醒,伸手一摸,整个人都僵住了。额头和脖颈滚烫得吓人。
时之序听到有人叫她,迷迷糊糊睁眼,脸颊泛红,眼神虚浮。江燧慌忙给她喂了退烧药,又拧了毛巾敷在她额头上。可半个小时过去,温度丝毫没退下去,反而越来越烫。
江燧坐不住了,盯着床边的温度计——三十八度九。他担心时之序是中了新冠或流感病毒,俯身拍她的肩膀,低声哄着:
“醒一醒,咱们去医院。”
时之序却像陷进热浪里,声音模糊:“不想动……头好重……”
他迅速拿起外套给她披上,一边拿上车钥匙,一边暗暗骂自己为什么没早点坚持送她去。
江燧几乎是半拖半抱半背,把时之序送到了急诊。夜里的医院灯光冷白,走廊安静得只剩下推轮床的轱辘声。他心里揪成一团,挂号、抽血、做快检。时之序头脑晕乎浑身没劲,但神智是完全清楚的,她劝江燧别急,等结果的十几分钟不至于会死。
“来,喝点热水。”江燧有点自责,就不应该同意淋雨回家的提议。
他太知道时之序看似理智的外表下,其实藏着贪玩而冲动的一颗心。旁人或许以为他们俩之间踩刹车的人是她,但其实往往是江燧。
他们并排坐在医院的软座椅上,时之序接过纸杯喝了一半,然后在江燧的怀里寻了一个舒服的位置倚靠。她脸颊微红,额角汗湿,偏偏还要开口调戏他:
“你也好hot啊。”
“……看来精神还算好,有空骚扰我。”江燧止住她在胸口作乱的手。
时之序闭着眼睛,迷迷糊糊地念叨着:
“摸自己男朋友……怎么算骚扰呢,何况你不是普通男朋友。”
服了,什么跟什么啊。
“你还有一个不普通的男朋友?”
她摇摇头,趁机又摸了一把胸肌,“你是老公级别的。”
江燧见过喜怒哀乐、爱恨痴嗔各个版本的时之序,但生病的她,他是第一次见。他才知道生病时她话很多、腻人的情话尤其多。时之序的牙尖嘴利和甜言蜜语是一体两面的,都来自她的聪明和残忍。
“怕我扔下你不管,所以故意哄我是吧。”江燧伸手又试了一下她的额头,仍旧烫得厉害,又轻声说:“别说话了,喉咙不难受吗?”
“没哄你。”时之序坐直了看他,撇了撇嘴。
“那你说说什么时候答应我的求婚?”
她愣住,真以为自己烧糊涂了。
“你什么时候求婚了?”
江燧的眼神里写满了惊讶和怀疑。他做人这么失败的吗?鼓起勇气向珍爱的人求婚,对方居然都不知道那是求婚。
时之序头脑轱辘转起来,求婚?是在和她家人吃完饭、她从车座里掏出戒指盒的时候吗?
两人还没来得及对账,就听到发热门诊里医生叫了她的名字。结果出来了,流感合并上呼吸道细菌感染,需要打几瓶点滴。
护士指示江燧去大厅里缴费取药,引着时之序到病房挂水。
她靠在病床上,额头的热汗擦了几遍,脑子里都挥之不去“结婚”这两个字。
二十七年来,她从没认真想过这件事。也许是因为从小近距离看过婚姻如何把时岚摧毁,也许是因为书里说得太清楚了——婚姻往往是另一种形式的占有,会把女人的身体、自由甚至灵魂都消耗掉。
这些想法听起来虚浮,可她不是没在生活里尝到过滋味。
和成昶同居那段日子,她才真切地明白,就算没有纸面契约,那种不对等也会悄无声息地钻进柴米油盐里。谁洗碗,谁刷马桶,谁忍着情绪不吭声……一切都能成为拉扯和消耗。
她从来不享受这些琐碎。那时候她就知道,承诺不一定带来永远,但一定意味着束缚。
可矛盾的是,她又偏偏喜欢永远这个词。在所有人类能够触碰的、最接近神的爱的体验里,她愿意相信,自己和江燧之间,或许真的存在一个“永远”的可能。
江燧端着一袋药和收据走进来,看到她靠在床头睁着眼愣愣出神。
“怎么了?”
时之序眨眨眼,把情绪藏回去,懒洋洋地说:“在想你为什么想结婚。”
江燧愣了下,没立刻回答,只把药放到床头柜上,替她把掉下来的被角掖好。过了几秒才开口:“只是想和你在一起而已,不是真有多想结婚。”
“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?”她故意问。
他没再解释什么,只是伸手按了按她的肩,把她轻轻按回枕头上:“躺下,别想了。睡一会儿,我帮你盯着输液瓶。”
点滴瓶里的药水一滴滴往下落,像夜色里最细密的雨声。困倦渐渐漫上来,体温渐渐降下去。
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没有再聊过关于这个话题,主要原因是忙碌。
时之序隔了一天就出发去了南京,签完访问学者的合同,原本想直接回岭澜继续做访谈,可耐不住林璐瑶一通电话,说自己特地请了年假,就是要拉她出来透口气。
于是她们临时改道,结伴跑去了上海玩。
七月的上海迪士尼热得像个烤箱,可以把任何生物都晒成躺在地上的脱水咸鱼。时之序刚进园没多久,就怀疑自己灵魂要从体内蒸发出来,林璐瑶更是抱怨连连,一边拿小风扇往脸上吹,一边嚷着“不会热死在这了吧”。
但乐园里依旧人山人海。卡通城堡闪着宝石般的光泽,巡游的花车在阳光下折射得眼睛发疼,忍过排队的几十分钟、幻影造的梦依然让人愿意再等下一个几十分钟。
林璐瑶咬着手里的冰棒,忽然笑道:“虽然快三十了,我还是愿意相信童话故事。”
时之序笑笑,伸手递给她纸巾:“童话故事的哪个部分?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?”
“当然不是!”林璐瑶做出反胃的表情,两人对视一眼、笑作一团。她接着说:“是勇敢和善良的人会有好报,心术不正的坏蛋会倒大霉!虽然童话故事里女人的‘好报’总是奖励给她一个好男人,但那太狭隘了,我想要的比这多得多!”
“真好,果然是你。”时之序由衷地感叹。她一直都很羡慕林璐瑶,羡慕她看待世界的方式,总是乐观而明亮。
“其实也很简单。‘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,种点土豆,做几个美梦。’”林璐瑶忽然改变音色,笑着学小孩说话。
时之序反应过来,“这是姆明说过的话!”
“Bingo!”林璐瑶得意地打了个响指,“姆明早就告诉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。”
夜色完全降临,迪士尼的城堡被灯光照亮,像糖霜包裹的梦境。她们席地而坐,在迪士尼城堡前的广场上,等待狂欢落幕前最后的烟花秀。空气中的热浪逐渐散去,人群却越聚越多,欢呼声此起彼伏。
时之序的目光落在林璐瑶的脸上,似乎欲言又止。
林璐瑶立刻捕捉到,歪着头笑:“你先别说,让我猜猜你打算说什么!”
时之序点头,示意她试试看。
“江燧向你求婚了。”她几乎没有任何思考就脱口而出。
时之序愣了愣,眉头一挑:“不是吧,他难道提前跟你说过了?”
林璐瑶笑得神秘,但连忙摆了摆手。
“没有没有,我只是猜的。”她想了想,继续道,“但我一直都觉得,只要你们有机会重新在一起,以后来我对江燧的了解,他肯定会想要快点和你结婚。”
时之序露出疑惑的表情。
林璐瑶和江燧在同一个城市读大学,他偶尔会向林璐瑶打听时之序的近况。尽管林璐瑶从没背叛过她的嘱咐,不会向他透露一个字,但他们还是熟络起来。
林璐瑶曾经问他,时之序已经很久没回国,也和别人谈恋爱了,他为什么还是不放下。江燧似乎也没法完全解释清楚,但林璐瑶还记得他说的一句话。
林璐瑶清了清嗓子,正襟危坐,模仿江燧的语气:“他说,‘我和她之间曾经有过的爱,让我觉得即便明天是世界末日也没有遗憾。可惜明天不是世界末日,所以我要一直等下去’。”
时之序笑出声来,却又感觉眼眶泛酸。
“挺轴的,和你一样。”林璐瑶总结道,“他肯定觉得和你结婚会更长久一些,殊不知即便是已婚版的时之序也是绝对自由的。”
“三年离婚两次?”时之序打趣道。
林璐瑶噗嗤一笑:“是你的话完全有可能,没人能管得了你。”
烟花秀正式开始的音乐响起,第一束烟花划破夜空,像银色的箭矢直射云霄,然后炸开,成千上万的细碎火花四散落下,像无数细小的光尘飘散在空气中。时之序抬头看着漫天绽开的烟花,光影在她眼里跳跃,也映在林璐瑶的笑脸上。
林璐瑶突然回头,在时之序的耳边大声喊:
“做你想做的事,做你想做的选择,之之!不要害怕!”
时之序站在原地,感受到心脏的跳动似乎跟烟花的节奏同步,她也大声对着林璐瑶喊:
“你也是!璐瑶!不要害怕!”
她们突然都觉得这样热血的互相打气非常中二,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,笑完了又拥抱在一起。
散场之后回到酒店已经快十二点了,两人累得瘫在床上,却仍有说不完的话。
时之序一整天没怎么回江燧的消息,这会儿林璐瑶去洗澡了,她才拿起手机给江燧打了个电话。
他给她带来的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:
老城二期拆迁的补偿方案重新启动协商了,将之前没有补偿资格的“外嫁女”们全部列入了补偿对象名单。但平均的补偿金额有所下降,有人开始抱怨,说是因为“外嫁女”也有份,所以大家的赔偿都少了。
时之序眉头紧皱,赶紧掏出笔记本来,又问了江燧几个细节问题,脑子里浮现出各种要推进的访谈和资料收集。
她还在边做笔记边思考,突然听到电话那头的人问了个很突兀的问题:
“想我了吗?”
时之序愣了一下,诚实说道:
“一点点想。”
她听到那头有抽油烟机运转的声音,江燧的语气变得亲密而柔软:
“我很想你。你才走了三天,感觉真是度日如年。”
他顿了顿,继续说,“也没什么办法缓解,所以大晚上起来炖鸡汤。”
“炖鸡和想我有什么关系?”时之序被他逗乐了。
“当然有,” 江燧低声道,“炖鸡的时候会想象你明天回家,尝到第一口的样子,我会提前感觉幸福。”
时之序心下怅然,她确实一忙起来就没怎么想江燧。
但现在她也体会了什么是归心似箭。原来馋起一碗家常清炖鸡汤的时候,连国际大都市的米其林都会黯然失色。
--
江燧:拿捏女人的心,首先要拿捏她的胃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