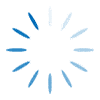蕙宁静静坐着,眉目间有隐约思绪流转。温钧野见她神色安静,到底还是忍不住开口,声音里带了点迟疑的好奇:“你表哥,是做什么的?”
她低头,银剪子“咔”地截断丝线,动作温柔细致,想起陈轻霄,笑容一下子变得真切起来,眉眼弯弯的,有几分久别重逢的亲切和感慨:“表哥不是什么大人物,叁年前会试落榜,心里不服气,就出去游历了。现在估计是玩够了,想回来了。”说到这里,她顿了顿,目光落在温钧野身上,带着点笑意:“他也是习武之人,说不定你们还能切磋切磋。”
温钧野听她话语轻描淡写,却听出来那份亲近与欣赏,他哼了一声,嘴里嘟囔着:“那得看看他武艺如何了。”
蕙宁声音柔和下来:“表哥不只是会武,还会酿酒。我从前送到府上的梅子青酿,就是他亲手酿的。他还喜欢做饭,不过每次下厨,总要来我这儿讨一双新鞋穿。说是穿着我做的鞋,才算有家的感觉。”她说着自己也忍不住笑了,旧日温情轻轻漫上心头:“小时候他还说,等我成婚那天一定赶回来。可惜这次赐婚太仓促,他也没赶上。”
温钧野这才意识到,自己竟然对蕙宁知之甚少,他下意识开口:“那你父母呢?”话音刚落,心里便咯噔一下。若她父母健在,婚礼上怎会不见踪影?这般问话,分明是触了人心头的疤。
他懊恼地抬手拍了拍脑门,眉头拧成一团,嘴里嘟囔着:“我这嘴,真是……”说着索性抡圆了胳膊,给了自己一巴掌,力道还不小,脸上立时浮现一片红痕。
蕙宁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,急忙伸手去拦:“你干嘛好端端打自己?”
檀云和绛珠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,紧接着又觉得有些好笑,忍着笑意听蕙宁吩咐,准备去拿消肿的药膏。
温钧野连连摆手,连说不用,脸上还带着点不好意思的赧色。
蕙宁沉静片刻,还是开口:“其实也没什么。我爹原本在徽州做布政使司,与我舅舅有些交情,因而得以与我娘亲相识。外公觉得我爹忠厚君子,便允了这桩婚事。成亲后,娘亲随我爹回了徽州,第二年我出生。可惜好景不长,我九岁那年,徽州大水,我爹亲自带着人去加固堤坝,日夜操劳染了风寒,转成肺痈,没多久就去了。”
屋内灯光映着她的侧脸,眉眼温柔,唯有眼角那一点微光,像是夜色里未干的露珠。她接着道:“我娘自此一病不起。听人说她哭了整夜,眼睛都肿成核桃。有一天清晨,她忽然咳血,没多久也走了。外公见我可怜,就把我接回京里,照应我这些年。说是外孙女,其实待我比亲闺女都亲。”
温钧野听她讲得淡然,心里却泛起一阵涩意。他嗓子有些发紧,粗声粗气地安慰道:“算了,这事就别提了。”
蕙宁低头轻轻叹息,语气温和,像是替他、也替自己宽慰着:“其实都过去许多年了,如今说起来,只是感伤罢了。再说,有外公陪着,我也没觉得缺了什么。我是真心敬爱外公,他也一直疼我。”
秋夜静谧,风过梧桐,叶影斑驳,落在窗纸上,宛如一幅水墨画。温钧野靠在床头,双手枕在脑后,望着屋顶的横梁出神。白日里昏睡得多,夜里反倒没有半分睡意,回想着和蕙宁的交谈,只觉得心里沉甸甸得,说不出的滋味儿。
赵夫人原本是让蕙宁在吴府多住几日,说是新妇初入门,总得安顿安顿。可蕙宁第二天一早便收拾好细软,与温钧野一起回了国公府。吴祖卿自是又给她备了一大堆东西,一些是送人的礼物,一些则是单独给蕙宁得。
回到国公府,秋阳尚好,天色澄澈。蕙宁换了家常衣裳,卷起袖子,亲自整理博古架上的摆设,边上还堆着一大箱子书,有些是医书,有些是旧年间留下的诗稿。
赵夫人进来的时候,正见蕙宁给架子上的摆件分类。赵夫人唇角含笑,轻敲了敲门框,语气里带着几分打趣:“怎么,一回来就这么忙活?”
蕙宁闻声抬头,见是赵夫人,忙将手里的活计放下,快步迎上前,神色恭敬:“娘亲您来了。快请坐。都是丫头们不顶用,您来了也不晓得通报一声,真是锯了嘴的葫芦。等会儿我一个个收拾她们。”
赵夫人含笑落座,神色慈和地看着蕙宁,见身旁丫鬟端上新煮的茶汤和各色点心,便随意挥了挥手柔声道:“不妨碍,是我让她们别来打扰你。你刚回府,省得被一群人围着头疼。”桌上的点心小巧玲珑,色泽诱人,糕面点缀着松子与花瓣。赵夫人随手拿起一块,细细端详,笑道:“这点心瞧着新鲜精致,是从你们吴家带来的吧?吴老先生最是疼爱你。”
蕙宁点头,温柔地笑:“正是。还有些小物件,原想着等会儿分送到各房,可巧您先来了。”说罢,她起身从锦盒里取出一柄叁镶玉的如意和一副素色药玉护腕,双手奉上:“娘亲,这如意寓意吉祥,护腕是些新巧玩意儿,还请您莫要嫌弃。”
赵夫人接过如意与护腕,玉石温润,秋光下仿佛氤氲着一层淡淡玉辉。她把如意在掌心细细摩挲,又笑着将护腕戴上,略感新奇:“我这粗人,平日只会摆弄些家务,这如意倒像是供着的宝贝,怕是会被我糟蹋了。倒是这护腕,巧得很。”
蕙宁轻声解释:“这护腕夹层里封着川芎、艾草等药材,常温下能慢慢透出药香。医书上说,玉与药气相通,能顺气活血,缓解筋骨劳损。娘亲您日常事多,戴着能养养身子。”
赵夫人听了连连点头,爱不释手,眼中满是欢喜:“你这孩子,心思细腻,总能想到这些。”说话间,笑意盈盈,叫身后的嬷嬷将一摞子账本捧上前来,放在蕙宁面前。
“我来找你,是有件正经事。”赵夫人将账本轻轻理顺,语气温和又郑重。
蕙宁见状,正襟危坐:“娘亲请吩咐。”
赵夫人看着她:“你也知道,家里头这些年一直是我在操持。你大嫂出身高门,不懂这些,你二哥二嫂搬出去住,自然是不会插手。老四老五年纪还小,指望不上。如今我年纪大了,精力也大不如前,许多事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你年纪轻轻,却最是细心聪慧,所以想请你帮衬着管管家务。”
蕙宁闻言,着实有些意外。出嫁前,赵夫人曾和吴祖卿提过,待她稳妥几年再让她接手国公府中馈。蕙宁本以为少说也要叁五年,且头上毕竟还有两位嫂子,轮也轮不到自己。没想到赵夫人这般爽快直接地把账本送到她手上,语气里既有托付,也有信任。
蕙宁连忙谦逊道:“娘亲,这事太大。我在外祖父家虽也理过家务,但终究是外公做主。我只是打下手,哪里敢自诩有多少经验。国公府家业庞大,规矩又多。大事儿还请娘亲定夺,我只敢跟着学学,哪里能擅自做主。”
赵夫人将账本往前推了推,语调宽厚:“你做事向来稳妥。家里事无非就是钱粮、下人、田庄、铺子这些,你先看看,慢慢来,不懂的随时问我。你不要拘谨,也别怕做错。娘相信你,放开手脚去管便是。”
赵夫人刚走,蕙宁就吩咐檀云、绛珠把各房的礼物一一送去。夜色渐深,蕙宁正和温钧野共进晚饭,忽听下人来报:“董姨娘带着一双儿女,来给叁少奶奶请安。”
蕙宁轻轻放下碗筷,和温钧野说了句“你先吃”,随手拢了拢鬓角,唇边漾起温和的笑意,起身迎了出去。董姨娘一见叁少奶奶亲自迎出来,顿时有些受宠若惊,忙不迭地福了一礼,语气里带着些许慌乱和感激。
“姨娘快请进。”蕙宁微微欠身,从容地将叁人让进了屋。
董姨娘的气色不算太好,眉宇间隐约有几分病色。她右手轻轻护着女儿温简容,左臂后挽着稚嫩的儿子温钧逸。叁人站在灯下,剪影温馨而略带拘谨。董姨娘小心斟酌着言语,低声道:“叁少奶奶,您送的这些礼物,实在是太贵重了。我们……我们实在受之有愧。”
蕙宁成婚的时候,她送的礼物自己觉得贵重,可是在人家眼里怕不过是些便宜的玩意儿。可现在雨丝锦、葡萄纹鸾镜,还有些贵重钗环,都是董姨娘没见过的新奇东西,简直是看花了眼。
蕙宁莞尔一笑:“姨娘快别这么说,您是长辈,我理当敬重。些许礼物,不算什么,您无须放在心上。”说着,她亲自斟上一杯热茶递到董姨娘手中,又取了几盘新鲜的蜜饯和果子,摆在两个弟妹面前:“我新进门,对弟弟妹妹们也还不大熟悉,不知两位喜欢些什么。下次,再给你们挑些更合心意的礼物。”
五妹温简容衣着素净,身形纤细,怯生生地看了蕙宁一眼,目光里带着几分新婚嫂嫂面前的忐忑,又藏着一点孩童的好奇。她小心地接过蜜饯,轻轻咬了一口,甜蜜的滋味在唇齿间化开,忍不住又伸手去拿了一颗。
温钧野这时也已放下筷子,耐心聆听。
董姨娘叹了口气,眉宇间满是母亲的担忧与无奈:“钧逸生性调皮好动,这些日子天天吵着要骑马。我怕他年纪小,不慎摔伤,一直不敢让他如愿。容儿性子腼腆,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,只喜欢听些小曲儿。”
蕙宁闻言,眼中闪过一丝了然,语调亲切:“正好我那里有一本康灵徽的《子夜四时变曲》,改日送给五妹妹。”
董姨娘急忙摆手,话里带着几分自谦和惋惜:“那实在太贵重了。其实、这爱好,也算不得什么正经事,怕是将来被夫家笑话了。”
蕙宁认真道:“姨娘这话可就值得商榷了。娘亲的妹妹,宫里的昭妃娘娘,不也凭借一副好嗓子得皇帝宠爱?康灵徽还是前朝贵族康家出来的女儿,就因为那本曲谱,得了天子赞赏垂青。每制新声,市陌传抄,竹肉相发,昼夜不绝。后来,还因此与崔家公子成就了好姻缘。怎么能说难登大雅之堂呢?”
她说着,目光柔和地望向温简容,笑意里带着鼓励,抬起手为她正了正小巧的绢花:“至于未来的夫家,若那人不喜欢,那就找一个不会笑话五妹妹的夫君。若是公婆不喜,便找一户没有公婆的人家。总归天高地阔,良缘自有归处。谁还要去在意旁人的流言蜚语呢?”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